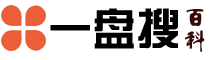装潢怎么读
王铎《字牖》卷四题识 清顺治刻本 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书库藏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2年第3期, 责任编辑王伟,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王铎与周亮工存在较为频繁的文艺交往,他们的书法创作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字体杂糅”。前者以楷书、隶书写篆籀结构,被时人称作“奇字”,后者则以篆隶书写楷书或行楷书结构,被王弘撰称为“以分为楷”。这两种创作模式在创作观念和形式表现上既相联系又有所区别,并延伸至此后的清代碑学发展脉络中,尤其两种字体之间的“过渡性字体”,实为碑学书派重要的探索方向。值得重视的是,在书法职业化出现之后,字体杂糅所带来的“古意”,在书法人群中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划分。而20世纪以来,随着唐以前墨迹大量出土,介于篆隶、隶楷、隶草之间的字体,其历史面貌日益清晰,字体杂糅所能激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逐渐消歇。
传为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提到,一流草书除钩锁连环之外,“亦复须篆势、八分、古隶相杂”1。王羲之是新体的重要推动者,这篇文章不太可能出自其手,但出现的时代不会晚于六朝。与此观念一致的是,初唐孙过庭认为真草二体需要“傍通二篆,俯贯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飞白”2。不过,从晋唐流传下来的楷书与草书作品来看,无论《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还是《书谱》,对书家的训诫与其说是字体杂糅,不如说是对书写技巧复杂性的要求3。
北魏至初唐的碑刻也出现过像《李仲璇修孔子庙碑》那样篆、隶、真书杂陈的现象。欧阳修已注意到,但未加解释。朱彝尊认为该碑杂大小篆、分隶于正书,是因为北魏太武帝始光年间新造字千余,致使一时风尚乖别。有学者认为这种杂掺字体的写法不过是掉书袋习气,也有人认为与北朝后期书坛的复古风气有关,而华人德近年的研究更具说服力的表明,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宗教的原因4。
一碑之中杂见篆、隶、楷多种字体,与本文所讨论的字体杂糅并不相同。本文所说的“字体杂糅”,是指一件作品具有稳定的、可辨识的字体形态,但其中杂糅其他字体的字样、用笔或结字方式。与单一的字体相比,字体杂糅因为“不常见”,而带有视觉上的新意。
自觉地将字体杂糅作为书法创作的手段并形成一种模式,始于明末清初。其时书家开始以晚出的字体用笔来写较早的字体结构,或以较早的字体用笔与结构来改写晚出的字体。这两种模式之间虽有联系,却不尽相同。王铎与周亮工是这两种创作模式的重要代表。本文首先勾稽王铎与周亮工之间的文艺交往,在此基础上,着力探讨他们书法创作中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字体杂糅现象及其不同内涵,进而论述这两种不同的创作模式在清代碑学以后的发展。
展开全文
一、王铎与周亮工的文艺交往
王铎与周亮工都是历仕明清两朝的贰臣,也都是艺术史上的重要人物。王铎是后董其昌时代艺坛的执牛耳者,在文学、小学、书法、绘画、鉴定诸领域都有重要的影响5。周亮工则被认为是清初最重要的艺术赞助人,其《读画录》和《印人传》旨在为当代画家与明中叶以来的印人立传,《尺牍新钞》则为当代文人立传。
王铎比周亮工年长二十岁,且都是河南人。作为同乡后学,周亮工在文艺上受王铎沾溉甚多。周的老师张民表与王铎为故交6,王对张颇为推崇,在写给范景文的信中曾介绍说:“大梁张林宗诗家董狐,伐毛洗髓于此道,足下料时晤对,服子慎、束广微、夏侯孝若、任彦升,殆其俦匹欤。”7服虔、束皙、夏侯湛、任昉是汉晋南朝著名的文人,王铎称张民表可与抗行。在考取进士以前,周亮工曾馆于张家八年,教其子读书,故对王铎之名并不陌生。
虽然崇祯十三年(1640)春日,周亮工进士及第,但王铎很快赴任南礼部尚书,并因丧父守制,从此远离京师,故二人可能要到弘光时期才开始频繁交往8。周在浚辑《藏弆集》卷八收录若干王铎致周亮工书札,很可能都作于彼时:
仆酒人也,花时多暇,同知己披观古图书汉篆,搦管快吟,肴核错至,酒一再行,醉矣。白眼望苍旻,翛翛然有出尘想。不知古人一石后与此何若?
仆老矣,晤对清阴,浣花扫叶,亦可乐也。回思促促金华中,不当为之一噱乎?
余书酒后指力一轻,如作山水墨画,笔过风生,诗歌从无意中辄得。壶卮间寝深卧言,疲命为勉作数字,不异枯鱼之索矣。如何如何。
牛首白云梯,松音鸟语,江声云影,登高骋望,颇无尘事相扰,此地书画相宜,选地莫此若耳。9
因缺少必要信息,我们很难考证各札的具体时间,但最后一札提及牛首山与周亮工的书画爱好相宜,选地以此为佳,当作于周亮工崇祯十七年南归之后。周亮工回到金陵,福王已立,时马士英、阮大铖用事,锦衣卫冯可宗诬蔑周亮工在李自成入京后“从贼”,故罗织下镇抚狱,虽“讯无佐验,复公官”,但马、阮又提出,只有周亮工弹劾刘宗周,他们才肯补用,周因而谢去,奉亲栖隐于牛首山10。从信中提到的聚饮赋诗、共同观摩古印、作山水画、为周亮工作书等信息来看,同在金陵的王、周二人时常相见,交流艺事。周亮工自称“亲炙文安公,奉教有年”11,指的应是这段时间的文艺交往。在另一封给周亮工的复信中,王铎写道:“岁月渐深,不晤为歉。辱承华讯,愧感集怀。向者敝庐分咏,大作高秀之气轶于尘表,风雅一道,今归栎下矣。无由面觌,渴思惄如。”12可知周亮工曾在王铎家中分韵赋诗,王对周的诗作颇为推重,但此时将近年底,二人无由会晤,周亮工屡有投札,王铎深感知己之交。
顺治三年(1646)之后,王铎在京任职,周亮工则游宦扬州、福建等地。顺治七年,时任福建右布政使的周亮工入京朝觐,与王铎再次相见,王有《会周栎园方伯》三首,自顺治二年南畿分别,六年之后再次会面,诗中提到的福建、开封与南京有二人的共同记忆:天启七年(1627)夏秋间,王铎曾主考福建乡试,此时周亮工主政福建,福建是共同的游历之地;崇祯十五年九月,李自成军围困开封,发生决黄河灌城的惨剧,开封是共同的伤心之地;顺治二年春夏间,王铎与周亮工在南京分别,南京是他们的结纳之地。“文奇亲友怪,语隐故乡同”13,不仅表明他们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与隐晦的故国之悲,也表明外界认为他们在文艺上具有共同特点——奇怪。
相见之际,周亮工将自己的诗集送呈王铎,求其作序。王铎嗣有一书与周亮工(图1):
闽峤乖隔久,为俱经大劫,蠛蠓过太虚,不必言,言之感恸。足下诗不意大有直,苍郁奇旷,铮铮骨格,不入轻薄促弱,中原吐气有人。坎坛中造物之贶足下多矣。昨夜痛饮香岩快友,吴儿佐觞,即不敢拟处仲击壶,而感慨悲歌,风雨鸡鸣,何啻呜咽,涕涔涔下也。兰金作好,千古论心,我辈一宵,便足胜他人伪交数十年耳。惠墨二豹囊,册子子夜操管,轻秀时习者多,生创、深厚、奇古良寡,近古,仆则题数语矣。仆今尚疐尾有日,太湖三万顷蒨峭广博,收入吾两人囊中,揽大海磅礴,作惊涛拍天语,誓果此言以毕著撰也,定不令奇山水笑人寂寂。报栎园老年翁诗社,王铎顿首。时五更含饛,仆催入署,火烘砚作书,笔秃其头毛,手冻冷甚。曹能始先生一大部诗选记心,舟中与仆,仆之饮食也。又顿首。14
“兰金作好,千古论心,我辈一宵,便足胜他人伪交数十年耳”,足见王、周二人殊非泛泛利益之交,而在心灵上有相契之处。读了周亮工的诗作,王铎赞赏他大有进步,完全没有“轻薄促弱”之弊,作为河南同乡,他庆幸中原诗学后继有人。信中还谈到周亮工委托王铎为他的一本画册题跋,王铎强调了他对松江派“轻秀时习”的鄙夷,而将“生创、深厚、奇古”作为品鉴的标准。同样作于本年二月的《赖古堂诗集》序,与这封信颇有重合之处,王铎历数明代以来的河南诗人李梦阳、张民表与张元佐,而周亮工乃继起之英髦,不仅观察八闽,具经济之才,其诗亦苍郁奇旷。王铎论诗文书画,均以气魄为上,因福建濒海,故信札与序言的最后都以“揽大海磅礴,作惊涛拍天语”15与周亮工共勉。
图1 王铎 致周亮工札 1650 纸本行书 四开,每开23.8×10.4cm 浙江省博物藏
王铎信中提及周亮工带来画册请他题跋,《读画录》对此有详细记载:
予庚寅北上,遇王孟津先生于旅次,阅所携册子,孟津最赏会公小幅,时年六旬,灯下作蝇头小楷题其上云:“洽公吾不知为谁,其画全模赵松雪、赵大年,穆然恬静,若厚德醇儒,敦庞湛凝,无忒无恌,灯下睇观,觉小雷大雷、紫溪白岳一段忽移入尺幅间矣。”又云:“是古人笔,不是时派,时派即钟、谭诗也。”小印模糊,误视会公为洽公,会公后即以洽公行,感知己也。16
王铎题樊圻画,亦收入《尺牍新钞》,周亮工注云:“予以樊会公所画呈先生,极蒙□赏,谓为江南一人。惟误会公为洽公,予欲会公竟作洽公,以志先生知己之感。”17王铎对金陵画家樊圻非常欣赏,认为他的山水胎息于宋元时期的赵令穰与赵孟頫,气格醇厚,具足古意。因为王铎将樊圻印章“会公”误读为“洽公”,樊圻感其知音,遂以洽公自号,而成一段美事。
事实上,樊圻画作只是周亮工送呈王铎的画册中的第六幅。王铎的题跋全部收入了他的文集:
《题槔园册》:画不欲凡,凡矣,即极意蚳笔淡墨,终是胶山绢海,非真山面貌,有补缀痕也。运笔不见元气磅礴,还之造化奇创,重开五岳,岂曰独以清、远、隘、小自喜,更足胸吞湖山乎。
《四幅》:虚碧相映,孤危峭崄,阖阳辟阴,有道存于其中。紫绿变幻,皆为外象。
《五幅》:涉江陈氏为柱下史,于兵火后游心图画,烘染全不卤莽,润莹婉约,可以知其微尚之所存。
《六幅》:洽公吾不知其为谁,此幅全模赵松雪与大年。穆然恬静,又如德厚淳儒,敦庞湛凝,无忒无恌,灯下睇观,觉大雷小雷与紫溪光景忽移于尺幅间矣。18
这本画册就是前引王铎信札中所说的“册子子夜操管,轻秀时习者多,生创、深厚、奇古良寡,近古,仆则题数语矣”。可见王铎对册中大多数画作并不满意,因此只选择性地题写了数件。其中第六幅为樊圻所作,第五幅为金陵画家陈丹衷所作,第四幅作者难以悬测。在第一幅的题跋中,王铎几乎将自己对时流的不满倾泻而出。这件我们不知作者的山水画,王铎认为了无真气,虽然讲求墨色,仍是“胶山绢海”。从“清、远、隘、小”的评价,不难想象是松江一派的作品,在王铎看来,松江派的画与竟陵派的诗都是时流,清秀薄弱,气格卑下19。
王铎的书画鉴定在明末清初有“董狐”之称,不唯袁枢、戴明说、孙承泽、李元鼎、王鹏冲、曹溶等人收藏的宋元名作多有他的鉴定题跋,他对同时的画家也极为重视,盛赞莫是龙、张复、张宏、左桢与赵澄等人的画作直追宋人,并四处搜求他们的画作。翁万戈旧藏的一套十八开的明人书画扇册,上款都是王铎所题,应是他有意装潢成册的。或许受王铎的启发,周亮工也大量收藏时人画作,并梓行《读画录》一书。王时敏《跋周栎园公祖时人画册后》有云:
少司农栎园周公……于文章政事之余,又旁精画道,流悦图绘。凡海内缙绅韦布、道人衲子,从事丹青,寓兴盘礴者,无不邮驿搜罗,重茧购索,积集有年,装成凡二十册,锦贉绣褫,标识其美,启函披玩,如探玉圃珠林,诡态幻思,缤纷夺目。此固艺林盛事,非公托寄高远,不能有此。20
周亮工同样将搜罗到的当代画家作品装裱成册,其20册的规模应远超王铎的庋藏。这些集册为这个特殊的时代留下一份难得的档案,明清易祚之后,周亮工的这一行为所体现的当代关怀,应不止耳目之玩而已。
周亮工与王铎三弟王鑨、次子王无咎也是挚友。康熙五年(1666),王鑨以山东按察司佥事任提督学政,周亮工则任山东青州海道、江安储粮道,二人为同官。四月七日,周亮工为王鑨《大愚集》作序,称河南自王铎继起于李梦阳、何景明数君子之后,力洗前弊,悉出意匠,加之王鑨连镳而起,二人如同陆机、陆云,振藻有所不同。并说:“予既亲炙文安公,奉教有年,且与伯子学士藉茅同谱之欢非一日矣。今又与先生运邅回此中,扬扢风雅。予于先生伯仲纪群之间取益良厚。”21可见王铎父子兄弟一门,与周亮工皆为文艺之交。就在同一年,周亮工还与另外一位河南诗学后劲赵宾选王铎、王鑨兄弟诗成《孟津诗》十八卷,周亮工于七月一日作序:
孟津诗者,合选孟津王文安公与其介弟学宪大愚先生诗也。文安以海涵地负之才,骀荡纵横,启蛰振槁。其所著《拟山园集》传播海内,海内之士闻风而兴起者,亦既如岳之尚嵩、河之崇海矣。凡欲追溯风雅,自信阳、北地后,必推孟津。是时大愚先生接踵比肩,著作尤盛。22
在序中,周亮工还声称“予夙尝奉教于文安公,而又从大愚先生游且有年矣”23,可见王铎兄弟二人在诗文上都对周亮工有所影响。不过,周亮工认为王铎诗集所收诗作太多,不利于传播,“予乡王觉斯先生诗凡百余卷,卷帙既多,每遂不能流传。予欲删为数卷以行,匆匆东行,不暇及矣”24。《孟津诗》或即周亮工为王铎兄弟诗集所作的删节本。
总体上看,周亮工因与王铎同乡的关系,在崇祯十七年至顺治二年、顺治七年曾与王铎有短暂但频繁的交往。作为前辈的王铎,一方面欣赏周亮工在诗文上所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向他灌输以古迈俗的主张,鼓励他践行生创、深厚与奇古。而周亮工对王铎的成就相当服膺,在王铎去世之后,曾为其删诗刊行,以促进广泛的传播,他的文艺观念与实践也深深打上王铎的烙印。
二、王铎与周亮工书法的“字体杂糅”
相较于诗歌与绘画,王铎与周亮工讨论书法的材料甚为稀见,在一封写给王弘撰的信中,周亮工曾有一段珍贵的回忆:“尝记在都门语孟津先生曰:先生书从帖上写下来,亮竟欲写上帖去,先生为之绝倒。”25意思是说,王铎一生勤于临帖26,而周亮工不耐临帖,于前人继承不多,却企望成为他人师法的对象,此语或暗示自己更具开创性。
虽然传之今日的周亮工书作在形迹上与王铎差异甚大,但王铎对周亮工仍深具启发。周亮工收藏有王铎的书画,顺治七年春,他至少从王铎这里得到两件行书大轴(图2)27和一件画扇28。周亮工的书法也有对王铎亦步亦趋的一面,如《孟津诗序》乃据其书迹刊刻(图3),是一笔纯正的王铎体29。但本文探讨的并非周亮工对王铎书法的追慕,而是他们的书法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字体杂糅”,或许这也是外界将他们的文艺都归之于“奇怪”的原因之一。不过,同样是字体杂糅,二人开辟的创作模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图2 王铎 会周栎园方伯其一轴 1650 花绫本行书 193×52cm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
图3 周亮工《孟津诗序》(局部) 清康熙五年王允明刻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在传世的王铎隶书、楷书与行楷作品中,有很多今天看来比较陌生的字形(或称“字样”),这些字形被时人称为“奇字”,如李清曾说,王铎“喜作诗文,中多奇字。每客过,则出而读之,且读且解,谈宴无倦色”30,因为奇字太多,以至对客读己诗需要不断加以解释。王铎在弘光朝位至次辅,票拟是日常工作,《平生壮观》著录一件他的小楷“票拟”,顾复称其“端楷异常,无一笔古体奇字”31,言下之意,王铎平日所书颇杂“奇字”32。不过,他人眼中的奇字,王铎认为乃是正体,当日俗字汹汹,几夺正体之席,而正体反被人“讶为奇字”33。王铎曾以答客问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认为当今“字之亡半也,不学者替而祸于点画也,遵今之讹,犹尊鬼而不守其故”,使用讹字等于尊鬼,这是何等的罪责。王铎一再声明,他的努力并非务于奇怪,厌学者却偏偏短之曰“好奇”,于是他不得不果断回击:“非好奇也,好古也!”34

这里所说的“奇字”,其实就是古字。王铎的楷书(包括行楷)创作,无论是丰碑大碣还是题跋数行,都有大量的古文、篆籀字形的隶化与楷化,或为整字,或为偏旁,从而发展出一种新奇的字样面目。如崇祯十二年二月《赠王思任大楷卷》(图4),“於”“賦”“哉”“以”“也”“友”“西”“貴在”“人”“莫”“蘇”“天”“發”“矚”“龍”等都是篆字楷写35。崇祯十六年避难于河南辉县,王铎开始学习汉隶,不过其《三潭诗卷》(图5)仍是以隶体写篆书字形,如“潭”“靈”“深”“石”“然”“驚”“雷”“神光”“即”“與”“寒”“共”“天”“予”“素”“書”“學”“異”等都从篆书化出,而非隶定之后的字形36。
图4 王铎 赠王思任大楷卷 1639 纸本楷书 27×252cm 台北石头书屋藏
图5 王铎 三潭诗卷 1644 绫本隶书 27×261cm 辽宁省博物馆藏
即便临摹《兰亭序》或其他晋唐经典作品,王铎也不惮其烦地将其中的俗字一一加以改正,这在过去的临帖活动中十分罕见37。如他传世的四本临《兰亭序》(表1),“嵗”字有三本改为“歲”,“稧”字有三本改为“褉”(一本脱字),“領”字有三本改为“嶺”,“暎”字有三本改为“映”,“弦”字有两本改为“絃”,“揽”字有二本改为“览”,“由”字有一本改为“繇”38。虽然王铎言必称晋人39,但认为“羲、献不过姿之秀婉耳,画不知古也,未之学也”40。“姿之秀婉”是肯定他们高超的书写技巧,“画不知古”则批评他们多用俗字。在《临郗愔帖》的一则跋文中,他还为书家指明了具体方向:一方面书法必须宗法晋人,否则会堕入野道;另一方面,“必又参之篆籀隶法,正其讹画”41。这里所说的“篆籀隶法”,主要是文字学意义上的古字。
表1 王铎临《兰亭序》四种与王羲之《兰亭序》(神龙本)字样比较
王铎书法创作上的字体杂糅,与他的文字学修养有密切关系。他认为,晚明字学荒芜,日常用字“点画边傍,其讹也多”42,乃是国运不振的先兆。在所辑《字牖》一书中,他曾经说道:
字学之研析者寡矣,毫厘之差,遂致谬戾。即经学之讹字讹句,不可胜数。盖俗字、野字、吏书、商贾字及演义传奇一种邪书,浸淫以夺正体。43
在写给戴明说的信中(图6),他再一次强调:
《六书故》《说文》字皆有稽,所谓野字、吏书、市巷方言、稗官小说、僧道,稽诸经史,腓痹之疣耳。凡书,有经有外传也,三教书皆然。44
在王铎看来,晚明的官府、商业、出版、市井日用各个阶层的文字使用中都充斥着俗字,俗字挑衅正体的地位是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表征。他的楷书中杂糅篆隶字形,是对俗书、邪书的纠正与对正体的提倡,是为了“崇正黜谬,共敦大雅之宗”45。钱谦益在为王铎志墓时,就特别提到他于六书之学有振起之功46。
图6 王铎 致戴明说札 1646 纸本行草 二开,每开21×11cm 香港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藏
王铎当日的古字资源,主要是古代字书与典籍47,也包括一些金石遗迹。如在《北国学石鼓文歌》中,王铎表现出对篆籀遗刻的跂足顶礼48。他收藏有《礼器碑》《乙瑛碑》的拓本,还曾为《尹宙碑》《西岳华山庙碑》(华阴本、长垣本)等题跋49。与文徵明等人取法三国魏隶书碑版不同,王铎认为《孔羡碑》“体变为方棱,古意稍漓,开唐之蹊径”50,而“隶法本篆,根矩宣王《石鼓》,唐惟肥胜,筋骨蕴藉亡矣”51。与后代碑学书家相区别的是,王铎最为倾心的字体并非篆隶,且对其“古拙”的趣味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的书法中所展现的字体杂糅,主要是字形意义上的,而非书写意义(笔法结构)上的。
前文提及王铎与周亮工一起观摩古印,周亮工对文字学、隶书与篆刻的研究很可能得益于王铎的启发。他曾辑《字触》六卷,这虽不是文字学著作,而是有关文字故事的书,但徐芳在序言中特别谈到周亮工的字学功夫:“吾友周栎园先生多才嗜古,而工字学。”52在清初,周亮工还审定了《广金石韵府》一书并为之作序,序文最后谈到字学与书学的密切关系:“然则得是书之旨而存之,岂独象意而无讹而已哉,书法亦于是尽善矣。”53通晓字学,不仅文字不违背造字本义,书法也能因此臻于尽善。身逢清初隶书振兴的大环境,周亮工对隶书的美学趣味比王铎更有体会。
闽人宋珏擅隶书54,他曾在金陵生活多年并留下不少遗迹,周亮工少时就看过他的署书55。周亮工为孙承宗《高阳集》所作序言的写刻本是典型的宋珏风格56,而顺治十七年所书《情话轩近诗卷》(图7)中的隶书,面貌则在宋珏与王铎之间57。嗣后郑簠对周亮工也有所影响,周自称“素从谷口学书”58,其康熙九年的隶书《黄河舟中作》取法《曹全碑》,不无郑簠的笔趣59。在郑簠《临曹全礼器合册》的跋文中,周亮工曾将他描述为恢复汉法的第一人:
书法隶最近古,隆万间群学隶而规模形似,略无神韵,即文待诏诸前修亦实之方整,无复古人遗意。后人救以生运,渐趋渐下,遂流入唐人一派,去汉愈远……诗道之坏与书法相终始,似有气运焉,不可强也。汉碑惟《景完碑》最后出,然《礼器碑》未尝不流传于世,而三百年来世人若未尝见之者。谷口郑先生出,始大恢古人真淳之气,令人稍稍知古法。60
周亮工认为,文徵明虽然书史闻名,但他的隶书学三国碑,方板无味,隆万间的书家多学唐人,更是等诸自郐。郑簠取法《曹全碑》《礼器碑》获得巨大成功,也与明人隶书划出了一道鸿沟。虽然王铎等人早就指出,唐代隶书远不及汉隶古朴真淳,但此时这已不仅是一种观念,更成为书家们的实践。
图7 周亮工《情话轩近诗卷》的隶书 1660 纸本隶书 全卷207×19cm 山西博物院藏
与王铎一样,周亮工也致力于收藏,且在当时也有善鉴的声名61。除了当世的众多画家,他对篆隶名家、篆刻家也了如指掌,金陵郑簠、歙县程邃、吴门顾苓、安丘张贞等人都与他有密切的交往,而远在陕西华阴的前辈郭宗昌亦素为周亮工所关切。康熙二年春日,王弘撰第二次来到江南62,周亮工在其时的致札(图8)63中写道:
弟学古人而不得,徒弄虚脾,遗笑大方。老年翁爱忘其丑,使人惭愧无地……《礼器碑》是锺太尉书,末有楷书作“鐘”,此字当时通用,今图章家“锺山”亦作“鐘山”也。此碑运笔在有意无意间,郭胤伯以为汉隶第一,知言哉。幼时见贵乡王先生《涧词》于敝业师张林宗先生斋中,序文笔法学《景完碑》,当时极叹其工,盖近人极力学汉人,究只到得宋人《孝经》地位耳。惟此序不失汉人意,似即是胤伯书。老年翁曾见否?胤伯尚在否?幸示之(胤伯尊讳并求示)。“以分为楷”四字,山鬼技俩被老年台一口道破。弟非曰能之,窃有志焉。八分将变于楷之时,应有一种过文,老年翁以为然不?64
周亮工很可能只同王弘撰见了一面,即匆匆北上青州赴任。在信中,周亮工甚至只知郭氏字胤伯,而不知宗昌之名,他要求王弘撰告知胤伯的名讳,并提及他少年时在老师张民表家中所见王承之65《涧词》一书,序文书法远过时流,是《曹全碑》笔法,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不知是否为郭胤伯手笔66。惜今日所见《涧词》卷前序言已残,无缘一见。不过郭的隶书墨迹在《屈原九歌图》的引首与题跋(图9)中可以见到,确实一派曹全风味67。
图8 周亮工 致某人札 1661 纸本行楷 四开,每开26.2×24.2cm 故宫博物院藏
图9 郭宗昌跋《屈原九歌图》 1640 纸本隶书 全卷32.1×467.4cm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信中提到的郭宗昌是王弘撰的同乡,他是晚明重要的金石学者,收藏相当丰富,如东肇商所藏《西岳华山庙碑》(华阴本)后来即为其所有,他还藏有周秦两汉图章数千颗,著《松谈阁印史》,韩诗称他穷体字学,辨析毫芒,以篆籀为性命68。崇祯十一年至十二年,郭宗昌应召入都,与王铎、钱谦益等人有密切交往,二人皆曾题其《松谈阁印史》与《西岳华山庙碑》(华阴本)拓本。王铎跋《松谈阁印史》(图10)云:
图书一道,点画根萭,咸有本原。譬之海,江河导之由也。龙门砥柱,匪其所肇祖也。近代嗜古者尠,讹书乱画,纰谬畔哄,而周秦汉体骨血脉亡矣。年家丈华州胤伯郭君,善诗博古,以其余力罗搜前代图书,且镌篆沉郁嵚崎,则其淹雅鸿奥,恶可以一端尽欤。69
在这篇跋文中,王铎一方面强调周秦汉印章文字与正字的关系,另一方面盛赞郭宗昌不仅搜求前代印章,篆刻也沉郁奇特,体现出极好的古文字修养。在王弘撰的记载中,王铎对郭宗昌隶书也颇为推重,以为三百年来第一手70。值得重视的是,郭宗昌在《金石史》一书中以“不衫不履”来概括汉碑之妙,认为与传统帖学的旨趣判若江河71,故王弘撰认为郭氏昌明隶书与韩愈文起八代同功72。
图10 王铎跋郭宗昌《松谈阁印史》 1639 纸本小楷 13.8×10.5cm 上海枫江书屋藏
在前文引用的这封信中,周亮工认同郭宗昌以《礼器碑》为汉碑第一的看法。他十分推崇《礼器碑》,称其为钟繇手笔,认为对汉隶的复兴具有重大意义。在写给倪师留的一封信中,周亮工说:
仆每言天地间有绝异事,汉隶至唐已卑弱,至宋、元而汉隶绝矣。明文衡山诸君稍振之,然方板可厌,何尝梦见汉人一笔。《郃阳碑》(《曹全碑》——引者注)近今始出,人因《郃阳》而知崇重《礼器》,是天留汉隶一线,至今日始显也。73
《曹全碑》《礼器碑》都是最早对清初隶书产生重要影响的碑刻,周亮工将之视为“天留汉隶一线”,即通过对二碑的学习,汉隶可得以光大,文徵明以来的方板习气可以得到根除。
尤可注意的是,周亮工信中提到王弘撰深嗜其书,但这里所说的周亮工书法并非隶书,而是楷书。周氏楷书不是惯常的晋唐面目,而是为王弘撰一语道破的“以分为楷”。所谓“以分为楷”,即用隶书法写楷书,它所指向的不仅是在楷书中使用隶书的字形,更强调以隶书的用笔与结构来改写楷书。在周亮工的想象中,隶书与楷书之间应有一种过渡性的字体,所谓“八分将变于楷之时,应有一种过文”。虽然在他的时代,金石资源还存在一定的局限,但写出一种介于隶、楷之间的字体仍是其目标所在——他相信这种面貌在历史上存在过,只是相应的碑刻尚未被发现。这一创作的方法相当特殊,虽与王弘撰“笔笔有来历”74绝然不同,却让王爱慕不已。
事实上,王铎的隶书、楷书(包括行书)中除有一些篆籀字样以外,其风格并不难辨别,他的小楷多学晋人,大楷则兼及欧阳询与颜、柳,行书在二王、米芾与颜真卿之间。王铎并不着意在隶楷之间寻求一种过渡性字体的趣味,亦即一种以更为高古的用笔与结构方式来书写晚出的字体。在他的时代,隶书尚未成为热门,他虽然收藏汉碑拓本,也临写、创作隶书,但对隶书的趣味尚少发明。到了17世纪后期,汉碑迎来一个热潮,人们对隶书抱有的热情超过了其他任何字体。除了临学与创作,对汉碑的审美趣味也有了更多的关注。王弘撰甚至认为,隶书中有《礼器碑》,“不异楷行之有钟王”75。
周亮工因多见汉碑,亦多见当日名手的隶书,对汉碑的美学趣味与书写技巧比王铎更为熟谙。周亮工有一些隶书作品传世,但并非专攻,其存世作品大多为行楷。关于他这类作品风格的来历向来缺乏合理的解释,因为人们无法从楷书与行书的经典名作中找到相应的形式资源76。虽说周亮工与王铎一样,认同“汉魏晋唐之间以书名者,先通篆籀,而后结体淳古,使转劲利”77,但他对篆隶的运用与王铎颇有差异。如周亮工《秦淮同元润赋之一轴》(图11),尽管也有少量古字,如“气”“㝱”“㴱”“夗央”“
”,却已不是主要特征。通篇点画粗细反差不大,运笔充满了不经意,显得含糊而不确定,字形结构则是典型的横画宽结,一些左右结构的字如“楊”“眼”明显左高右低,这些都是他所理解的隶书旨趣。他也很少强化“钩”,这是隶书中没有的点画。将篆隶用笔与结字引入行楷书之中,篆隶与楷行在周亮工的作品中获得了另一层次的杂糅,其面目是楷书或是行楷,趣味却是篆隶。按他与王弘撰信中所说,自己的书法是隶楷演变中的过渡性字体。这种过渡性字体因为包含有隶书的用笔与结构意趣,从而打破了人们对楷书既有的印象。
图11 周亮工 秦淮同元润赋之一轴 绫本行楷 218.8×53.5cm 故宫博物院藏
康熙初年,书坛不仅出现了周亮工这样的探索者,也有了王弘撰这样的欣赏者,这说明此时涌现的新的书学资源,不断刺激着书学观念与创作实践的新趋势。尽管周亮工字体杂糅的实践还远称不上凝练,但他打开了一扇远比王铎宽阔的大门。
三、清代书法中的“字体杂糅”
毋庸置疑,明末清初出现的字体杂糅,是其时以古迈俗的书学追求的结果,但这种开放的字体意识为此后的书法探索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方向。如前文所述,王铎与周亮工的书作虽然都有字体杂糅的现象,但其意涵并不完全相同,在观念与形式上存在较大差异。在清代,这两种创作模式也有着颇不相同的影响脉络。
王铎杂糅字体的创作方式在晚明并非孤例,他的同年进士黄道周、倪元璐的书作中也常有篆书楷写或是隶写的情形78,当时既有人称他们“法兼篆隶,笔笔可喜”79,“览之几如三代鼎彝,两京文物”80,也有人不以为然,郭涵星就批评王铎“好奇用古字,雅称述古,其愈失矣”81。顾炎武虽认为初唐碑版尚有八分遗意,正书之中往往杂出篆体82,但也认为“舍今日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盖其俚浅也”83。冯班更针对王铎的用字发表议论:“作书忌俗字,人皆知之。不知亦忌古字。”84
尽管时人对王铎等人以隶体写篆籀结构,或以楷、行写篆隶结构的创作方式意见不同,但稍晚于他的陈洪绶、傅山、周亮工等人都延续着类似的习惯85。在陈洪绶的行书《诗翰》(图12)中,“答”写为“畣”,“乎”写为“[孚] [丁]”,“國”写为“圀”,“風”写为“凮”,“莫”写为“
”,“剩”写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