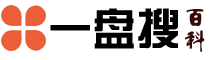马铁丁,回忆在赤峰的日子 ——访郭小川夫人杜惠
万壑松风——本名孙国辉 退休前曾供职市政协文史资料部门,热心学习赤峰近现代史料和摄影,曾出版《赤峰摄影史》及举办肖像摄影艺术个展,文学作品曾被国家及外省报刋选用马铁丁。


回忆在赤峰的日子

——访郭小川夫人杜惠

孙国辉文/摄影


旧历癸巳年腊月中旬的一天,笔者几经辗转,在北京见到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诗人郭小川的夫人杜惠先生。

见面的一霎那,我惊诧得几近失态。看上去六十许的老太太其实已经九十四岁高龄了,眼神那样明澈睿智,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矍铄中常泛起粲然的笑。即便是谈到所经历的坎坷和常人无法忍受的磨难时仍在微笑……不由使人想起明代升庵的《临江仙》中的:“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

(杜先生近影 孙国辉摄影)

(杜先生正接受笔者的采访)

我将我市李宝祥君送与的,在赤峰地区发现的郭小川同志生前给作曲家安波同志的一封水笔信(信的内容是他们一同创作的《毛泽东颂歌》中的一句词,郭小川“还想换一换”,故提出三个修改方案)的复印件,和冀察热辽联大鲁迅文艺学院编辑的,1948年6月1日出版的第一期《群众文艺》上郭小川写的“山乡小纪”之二“杜福”的复印件,一并送给杜先生。杜先生一眼就看出了郭小川用毛笔写信的笔迹,连连说:“是小川的字,是他的字……”那种鲐背老人的真挚之情,令人泫然。

继之我又将红山区政协编辑的《赤峰沧桑》送与先生,请她提意见。她专注地翻阅了一遍,特别将书中登载她与郭小川的合影仔细的看了看,直率地提出了几点意见:(一)这张照片是离开赤峰很久以后在武汉照的,最好是用在赤峰的片子。(二)照片上的说明说郭小川是1946年到赤峰主办《冀热辽日报》,1946年郭小川还没去赤峰,而是在丰宁任县长和打游击。到赤峰是在1948年9月。(三)以继承和发展延安办报的传统,成为冀热辽各报的榜样……”有失偏颇,因为当时边区只有这一份报纸,不存在其他报纸。(四)也不叫《冀热辽日报》,而是中共冀热辽分局的机关报《群众日报》。(五)郭小川不是主编,而是副主编。

笔者作为编纂《赤峰沧桑》的参与者,听此不禁赧颜,连连示歉。先生对此毫无芥蒂,带着微笑应我之请讲起了自己的经历。
先生原来姓邓,叫邓惠君,祖籍四川,住在成都上邓家巷怡怡轩。生于“五四”运动的第二年(1920年)。祖父、伯父和叔父在自流井制盐。父亲行六,原在铁道学院任教,曾在重庆郊区长寿女校当校长,还当过县里的建设局长。除了大伯父、二伯父是大盐商外,其他都从文,有的是文官。当时家里是四进大院,记忆中连厨房都很大,年年按着节令杀不少的猪,做很多腊肠、香肠、糯米酒、萨其玛、豆瓣酱……称得上大户人家,或者是殷实的书香门第。
(1956年春,杜惠与三个孩子在北京陶然亭公园,郭小川摄影)
“我先读了点私塾,后来上了新式学堂。在进步和革命力量的影响和感召下,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1939年19岁时光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中国,正在内忧外患,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犯的危机关头。我决心响应党的挽救民族危亡的号召,毅然离开家庭,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为了避免家庭的阻拦和敌人的迫害,我登上了成都到延安的火车,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名参加了八路军,后来到了延安,在延安女子大学学习。”
郭小川参加革命比我早。郭小川说:“家乡的沦陷、生活的困难,北平又时刻在危亡中,国民党的法西斯教育走向反面,引起我的反抗情绪,使我有抗日、反对蒋介石、宋哲元的黑暗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要求。”在北京求学期间,从1935年冬参加北京学生“12.16”游行示威起,便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白天和同学们上街贴标语,宣传抗日,还演出进步戏剧——莫泊桑的《项链》和易卜生的《国民公敌》片段;晚上回到宿舍刻蜡纸,印传单、出小报、读进步书籍。并参加罢课斗争。还因参加北平学生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并担当纠查队员而被捕关押了一天…..他参加进步组织,并开始写作新诗。如《追悼导师鲁迅先生》、《女性的豪歌》和《夏》……民族的危亡是中国革命之温床,对于郭小川来说,民族的危亡是有切肤之痛的,因之他衷心应和着革命的感召,怀着诗人的热情投向革命。
卢沟桥事变过了十天,郭小川就逃出北平,在太原参加了八路军。9月20日或21日,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同参军的平津学生谈话。翌日,他们便同王震、萧克、关向应乘火车到了忻州附近120师部,随王震到了定襄蒋村三五九旅旅部。11月7日郭小川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山西的两年里,他随旅政部的“奋斗剧社”到前方部队演出宣传,做扩军工作,做宣传员、宣传干事,连政治工作员,教导营的政治辅导员和政治教员。1939年三五九旅奉调到陕北绥德,他担任司令部的机要秘书,协助旅长兼政委王震工作。这一时期,他写了《牧羊人的小唱》、《滹沱河上的儿童团员》、《疯妇人》、《我与枪》、《骆骆商人挽歌》、《热河曲——忽然想起我的家》、《我们歌唱黄河》等。
参军前郭小川的名字叫“郭恩大”,参加八路军后改名为“郭苏”。在一次战斗中,郭苏获得一件战利品:一支精致的日本钢笔,上刻“小川一郎”字样。他对这支笔十分珍爱,遂开始用笔名“郭小川”。
当时,延安已成为全国青年向往的地方,为了抗日救国,他们冲破重重阻力,历经艰辛,怀了赤子之心奔向这一革命圣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延安吸引了来自国统区的大约四万余知识分子。1940年底,郭小川来到延安。他改变了去“鲁迅艺术学院”的初衷,进入中国共产党培养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构——马列学院。郭小川曾说这是“为了当作家而学习马列主义”。后马列学院更名为中央研究院,郭小川在其文艺研究室和汪琦、金紫光、天心、江帆、王实味等同为研究员,主任为欧阳山。后中央研究院又成为中共中央党校第三部。
这期间,郭小川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基础知识,还阅读了大量文艺理论书籍和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如《安娜▪卡列尼娜》、《被开垦的处女地》、《欧根▪奥涅金》…..
郭小川在散文杂篇《延安生活杂忆》中写道:
“这时候,延安最特殊的地方,便是延河两岸的男女了。因为女大在党校对面,每天晚饭后或假日,在延河边散步的颇不乏人。女同志的装束是蓝斜纹布服装,带耳朵的帽子,即使是好天气,也把耳朵放下。最讲究的要算围巾,花花绿绿,不过是追逐都市风而已….男同志最标准的服装是白碴短皮袄,颈上围布或毛围巾。那年发的鞋子很好,是高筒的黑色布棉鞋。很多人头发都挺长。”
“那时各校的生活并不好,很少吃馒头、肉,更多白水盐煮洋芋。吃饭是在露天的院子里,每一组一个瓷罐,小米饭常常挺硬。”
杜惠先生说:“郭小川常与三五好友在傍晚沿河散步谈心,朗诵诗歌,畅想未来,就在这段较为安定的日子里,我认识了郭小川。”
她深情地回忆:
我和郭小川是在1940年的初秋,一个晴明的日子里相识的。这次相识十分偶然。听说山下有人给我的好友荔带来一封信,我随荔一同跑下山来,见一个脸色微黑红润,中等身材、厚嘴唇,一身灰军装的青年战士,把一封信交到荔手里。荔看信时,他老老实实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表情憨厚地凝望着杨家岭山上那一排排的窑洞,显出若有所思的神情。
我发现他的军装未扣风纪扣,军帽耷拉着,像个农民出身的“土八路”。他两眼炯炯有神,双眉间很深的立纹,显出很爱思索的模样,倒也显出几分英俊之气。
荔向我介绍道:“他是我们这边的一位青年诗人,叫郭苏,笔名郭小川。”接着,荔转向他介绍着我,我们相互含笑点头,表示敬意,却彼此未说一句话,他匆匆告辞而去。
荔和我目送他向延河岸边走去,他步伐轻快矫健,有一种战士的英武,只是那八字步的脚,却给我留下了不够美的印象。从外表看不出他有多少才华,怎么会是个青年诗人呢?我心中有些奇怪。
次年元旦,小川来延安学习后,由于荔的关系,他经常到延河边同我们一起散步,我们很快形成了一群朋友的集体散步。我们相互谈一些国内外大事,谈文学和诗,谈友谊,谈爱好。我发现他的思想水平、风格和气质,与刚从国统区学校出来的许多青年不大一样。他热情、纯朴、宽厚、思想敏锐、朝气蓬勃、乐于助人,但不多言,不锋芒外露。
“我们这种天真纯洁的集体友谊交往与散步,从1941年初直到9月一直很平静,没有任何波澜。女大要并入延安大学,女大同学将被分到各机关学校去,跟女大同学交往的男同学都忙起来,准备赶快挑选自己心爱的姑娘。
小川后来告诉我,女大停办后,他和河南姑娘虹相约,单独在延河畔谈了三次心,彼此都很倾慕。几乎快要吐露求爱的心声时,小川却收回了自己的决心。为什么?小川对我说:‘特别使我心动的,是你有一种棱角。’他的友人也极力鼓动他选择这样的‘棱角’,再加上某种南方姑娘的气质吧,小川终于下定决心,把丘比特的箭坚定不移地射向了我。”
在1941年秋定情的那个晚上,我们向着青春般的小树林,向着永远欢唱的延河水,向着宽广美丽的星空宣告:“我们订婚啦!我们订婚啦!我们发誓:一定要像政治上永远忠于党、忠于革命那样永远忠于我们相互间纯真的圣洁的爱情!”
“1943年新年假期时,我和小川去看吴玉章老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早年参加民主革命,曾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一南昌起义中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后被派到苏联、法国和西欧工作。参加过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1938年回国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时已60多岁 ——笔者),向他报告了我们即将结婚的喜讯。他非常欢喜,为我们祝福,又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我说:没什么困难,只准备向组织上申请一床被子。他想了一下说:现在蒋介石、胡宗南封锁边区,我们物质上处处有困难,我来替你们想想办法吧!我看棉花可以向学校领几斤,被里被面就由我解决。这时吴老用干瘦有力的手,指着半壁窑洞上挂的那张细布的旧世界大地图说:这足够你们做一床很大的被子啦!我问:吴老,那你用什么地图呢?吴老说:组织上早就要给我换一张新的大地图,我想为公家节省下来,再用两年旧的,迟迟未换。现在好了,你们用我这旧的,洗净了做成新被子,我又换上了新地图,不是两全其美吗?吴老试试布的质量,说:还很结实的,够你们用几年的,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了,进了城,就可以换新被了!”
“吴老还送我们一副祝贺新婚的喜联:杜林深植惠,小水江为川。”
“春节前,小川在他的窑洞里用黄土泥堆了一对并排的沙发,还用铁片抹的十分光滑,铺上两张老羊皮,坐着很舒服的。在沙发上方墙上工工整整地贴着吴老送的喜联,床上放着那张世界大地图做成的被子。春节那天下午,我们举行婚礼,喜宴就是一大桶红枣绿豆粥,文艺理论家欧阳山(著名作家,后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广东文联主席,作品有《玫瑰花残了》《英雄三生》《一代风流》《三家巷》——笔者),党支部书记刘白羽(卓越的散文家,报告文学家,小说家,作家,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党支部书记——笔者)是证婚人。
隔了几年,郭小川有感于两人美妙的初恋,写了他一生唯一的半首情诗:
“八年,青春的季节,
爱情一直在那颗火热的心中激荡,
说不尽的甜蜜的往事,
一辈子咀嚼不完的袭人的味儿,
延河边上的冬天多么冷,
大风刮着,有一双温存的手
为我扣好皮大衣的钮。
在春天,野玫瑰的芳香,
使我们陶醉,不,那是我们并排
走着,不住的热吻,
巴尔干的夜,胸脯对着胸脯……
(“巴尔干”是延河边的一片山坡)
黄永玉先生在第十届巴金先生学术研讨会上以其令媛的一句话结束发言“文化人好脆弱,容易在大时代夭折凋零……”风信子先生说:“诗人都是敏感脆弱的。在与糟糕的世界的对抗中,诗人为了坚守个人的纯真宁可自戕。”延安给予郭小川的教育是触及灵魂的,当时恰逢他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青年时期。
到了日寇投降,郭小川奉命北上,8月13日晚,郭小川听了毛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三天后,就作为延安第一批干部队成员离开延安到了热河省。当时的省长发现他是本地人,便派他到其家乡,亦是急需干部的新区东丰宁县担任第一任共产党县长,而杜惠也分配到丰宁县任妇联主任。
后来杜惠怀孕了,依然坚持下乡工作。到1946年8月底,蒋介石将内战的炮火燃进热河,在毛主席“让开大道,占领两厢”的战略思想主导下,我军放弃了承德、锦州等城市,杜惠坐着硬轱辘牛车撤到郭家屯。杜惠和郭小川呆了两天,上级命令郭小川到热西打游击。杜惠已经怀孕八个月了,在兵荒马乱之中心情十分郁闷,郭小川安慰她说:“不管怎样,你在后方把孩子好好生下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等着你和孩子,即使被还乡团抓住,也不能有一点软弱,要坚强,不要担心我,我在部队待过,我能应付,我不会死。如果生的是男孩就叫小牛,因为鲁迅先生说:‘俯首甘为孺子牛’,若是女孩就叫梅梅,因为梅花能抗御冰雪严寒。”
杜惠随着地方机关的家属们连夜出发,所幸同行的有一位延安来的女医生彭克大姐,一行人撤到赤峰住了几天,又撤到热河与内蒙古交界处的林东、林西一带,当时算是我军的后方。
杜惠坐在头一辆牛车上,其他家属和保卫战士共20来人,专挑夜晚走,打着火把,白天住在老百姓家,这样夜行昼宿是为了避开土匪还乡团。
在抵达林西前的傍晚,牛车在崎岖的山路下坡时猛然一颠,将杜惠和行李一起掀下车,接着车轱辘从仰面朝天的杜惠大腿根轧过去,所幸杜惠的腿在两块山石之间的坑里,又穿得厚,幸无大碍,最幸运的是没有伤到孩子。
上级原来准备让这些人去东北,后来因为天气寒冷,前边另一只撤退队伍的车上冻死了几个孩子,就没有让她们再去东北。
在杜惠女士谈到生孩子的情况时说:
“当天晚上到达林西县的西林镇(笔者注:此说法显然有误,林西自清朝放垦至今,从未有此镇,然林西县境内却有一村名为新林镇,但杜先生在后面的叙述中又说她分娩于一回族家中,而新林镇亦因回族的民族习俗从未有回族居住,故先生所说西林镇应为当时的林西镇,即林西县。当时林西县的回族群众都生活在建有清真寺的十字西街),组织上特意为我找了一位可靠的老乡,家里就一位年轻妇女,是回族。我一进她家就掉眼泪,一是肚子疼,二是小川不在我身边……喝了点粥和红糖水,睡了一会儿,醒后又觉得疼,热心的大嫂赶紧找来了大夫彭克大姐。到后半夜两三点钟孩子生下来了,好心的大嫂及时地给我喂了米汤。一听到孩子的啼哭,我的抑郁立刻消失了,变得特别高兴,人家告诉我,生了个儿子,白白净净的,小手小脚红红的,挺可爱的,我喜欢的要命….这一天是1946年10月18日。”
“生完孩子第四天我们就转移去了赤峰,天气特冷。我因为生孩子,组织上特别发给我一顶火狐狸皮帽子,还发了一双很暖的靴子,还发了一件里面是羊毛,外面是绒毛的上衣,热了反穿,冷了再翻过来。抱着孩子坐在大车上总算走了过来,后来我把那顶非常暖和的皮帽子捐给了前方打仗的战士。”
“彭克大夫告诉我,军分区、地委都在赤峰,要把热河机关的妇女儿童送到东北去。因为这里又贫穷又不安全,所以要先转移到赤峰,再由赤峰坐汽车去东北。我就带着孩子坐牛车从林西到赤峰。路上连续三天一直抱着孩子,多年后胳膊肘还疼。到赤峰后,住在一个阿訇家,阿訇较老,还有一个年轻女人,我第一次吃到莜面,做饭的人用手指一搓就是一个面鱼儿;一手下面,一手抓牛粪往火里添,还要拉风箱,外墙上贴的都是一饼一饼的干粪。”
“分局给我找了一间房子。”
“程子华接见了我一次,告诉我小川在打游击,很坚强。程送了我一大桶美国奶粉,战利品。都由房东大嫂用开水冲了喂给小牛喝,我没尝过一勺。”
“组织上给我派了一个叫黄肇基的稍年长的男同志照顾我,人很忠厚,帮我生火打饭,很喜欢小牛。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小川没有消息,他曾对我说:你的郭是死是活很难说——在那个战争岁月,有这种想法很正常。后来保留下来的我和小牛的照片都是他给拍的,照片上小牛穿的衣服,戴的帽子都是美国军援品。”
“小牛几个月大时,组织上分配我去赤峰的建国学院的一个班当辅导员,校长是徐懋庸,有很多蒙古族学员,工作了不久,在徐手下工作不太愉快。”
“我有一个很小的通讯员,叫刘春林,十五六岁,很瘦小,什么也不会干,我对他不够耐心,嫌他笨,孩子也不会抱。一个多月就退掉了。”
“赤峰不久发生鼠疫,我们就南迁(至现元宝山五家镇 笔者)我就在附近参加了土改,做宣传工作,帮助农民分浮财。”(当时,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军区、热河省的政府等机关已从林西陆续南迁到现在元宝山区五家镇政府所在地和不远的望甘池村,《群众日报》社设在牦牛营子破落地主李树庭院内——笔者)
“我一直带着小牛,他七八个月会叫爸爸妈妈,一岁左右会走路。”
“土改后,我又回到了分局,还住老乡家,老乡给做稀糊糊。大概公家给他们一点点钱,作为我的伙食费,我记不得了,那时我既无工资、津贴,也没什么补助。”
过了两年,即1948年的4、5月份,郭小川披着战火和硝烟在赤峰南边的五家见到了杜惠,见到了孩子。郭小川说:“想不到小牛(后来爷爷为其起名郭小林,以纪念在林西降生)都这么大了,会叫爸爸,会走路了,突然有这么大的孩子,很奇怪的。”于是在欣喜中写下了一首诗:
“在伟大、光荣而又不幸的年代里
你诞生了。你来得正好呵,
你勇敢,没有被炮火吓住
你坚强,没有同母亲一同摔死
你就有福气听见
这里是轮转的尾声。
……在千里之外
你的父亲正在寒冷的乡村里工作着,
当他在工作的余暇
就会想起你的母亲和要生的你
可是,他一直担心着
你们的生或死……”
——诗残篇《祝儿子的诞生》
(郭小川在赤峰市五家村第一次见到儿子时的留影)
当笔者问及老太太建国后自身的经历和工作生活时,她仍微笑着对我说:“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1948年,郭小川进入新闻和宣传领域工作,前几个月在隆化,到夏季和杜惠一起调到中共冀察热辽分局的机关报《群众日报》。郭小川任副总编辑,杜先生回忆这段时间的经历时说道:
“到五家子村之前,小川已在地委书记韩德纯协助下办了三个月的土改内部刊物《新作风》,我带着孩子,一开始没工作,小川是副总编辑兼编辑部主任。每天从早晨忙到深夜,除了写短评,处理文件,还写社论,工作了五个月写了十几篇社论。”
(设在五家村的原《群众日报》社址)
“后来我开始编稿,不久成立《农民报》,小川任社长,我是见习编辑。工作后我把孩子放在我们大院对门的一户贫农家里。老乡家穷,只有野糊糊吃。不久那家人说,你这孩子咋总是捡地上的东西吃,甚至抠脚底板的泥巴吃,还白天晚上拉稀,老乡带不了,又没吃的,我只好接回来。”
“小林生病的村子就是五家子,往东五里的村子有分局的卫生所,所里有个外国大夫,胖胖的,四十来岁,人很好,英国人或澳洲人。可是那时条件太差,既没有药也没有医疗器械,无法化验,只能给点消化药而已。孩子的病情时好时坏,渐渐衰弱,脖子瘦的只剩一层皮,肚子鼓得老大,身上却没有肉,胳膊腿干干的,真可怜。”
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平津战役”要打响了,1948年12月初,我们接到通知坐上大卡车向关内进发。车子走到遵化、玉田之间时,组织上说要到白洋淀一带等候,何时进天津不好说,所以孩子要留下来,由组织上分散安排在老乡家,地点、老乡姓名,我都不知道。
“过年了,我想念孩子,和小川发生了龃龉。小川说:北平天津要解放,这么大的事在眼前,谈不到家庭这些事。打消了我的思想问题,也为他博大忠诚的革命襟怀所感动。”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的当天,由王元之、董东、范瑾、郭小川接管原天津《益世报》,第三天《天津日报》创刊,郭小川任《天津日报》编委兼编辑部主任。分管文学副刊,与方纪、孙犁同室办公。
“不久儿子小林由组织上派人从乡下接来,送进了天津幼儿园,园里带他到大医院看病,发现他长了虫子……小林的生命已经很危险,医生说,如果再来晚点,就活不成了,医生用药打下了虫子,让小林保养了一段时间,这期间一直不让我们去看。后来小川调到武汉中南局宣传部,我们俩一直期待着孩子的归来。过了几个月,孩子被送到武汉,接回来一看,小林长得又结实又漂亮,特别可爱。中南局的阿姨和姑娘们都喜欢他。”
“火车的笛声响了,再见吧,北方!
让我回过头再一次把你瞭望,
……
可,北方,我深深地理解你,
理解你今日的欢乐
也理解你过去的艰难……”
从1949年6月到1953年3月,郭小川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处长,后兼文艺处长。
毛主席1942年曾说过:“郭小川和他的好友,时任《长江日报》副编辑的张铁夫和时任新华社中南局分社副社长的陈笑雨开始在《长江日报》上开辟思想杂谈,”这一创意得到华中局宣传部长兼《长江日报》社长熊复和总编陈楚的首肯。
“三人从名字中各取一字,集成一个集体笔名“马铁丁”在两年时间里,署名马铁丁的小文章天天见报,总数达五百余篇。”
(“马铁丁”写下《长江日报》辉煌一页)
笔者闻此大喜。因为老人揭开了笔者多年来的一个疑窦,既马铁丁究为何人。笔者少年时虽顽劣,亦常常浏览报章,常见马铁丁的文章。那文章题材极广,内容多种多样,有政策解析,有时政评议,有问答,亦有谈心……在偌大的报纸上只占一隅,是真正的“豆腐块”般大小。每篇不逾千字,密切联系实际,有针对性,没有空议论,文笔又生动活泼,不以势压人,不摆架子,不说套话,以诚恳平等态度和青年朋友商量讨论问题。(黎辛语)当时的笔者对马铁丁之崇敬无以言表,甚至见到必读,读后再抄,笔者还曾长时间寻找他的文章。今天,从杜先生口中我才知道了马铁丁是谁,揭开了多年的一个谜团。
贺敬之为谭征著《寻找马铁丁》一书作序写道:
“马铁丁,这是一个闪光的名字,马铁丁杂文从影响读者的广度和强度来说,可以说是继鲁迅之后,杂文发展史上出现的又一次新的辉煌。”
恕笔者肤浅直言,后马铁丁时代的杂文,包括其他文体,再没有达到过那样的高度,假话、空话、套话充斥,颐指气使者有之,仗势欺人者有之,詈骂诟病者有之,无事生非者有之,杂踏冗赘者有之……悲夫,马铁丁的笔触已成空谷绝响。
一九五三年三月,郭小川奉调中央宣传理论宣传处任副处长,为此,郭小川兴奋异常,他在给杜惠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对于北京我已经对你说了很多很多,但是,我对北京的感情和对未来生活的幸福向往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我们都还年轻,来日方长,北京会给我们多少生活的灵感,多少喜悦,多少智慧啊!北海的秋波,五龙亭的风声,西山的红叶,昆仑湖的倒影,都是属于我们的,……”
——郭小川致妻子信1953.2.8
(中年时期的郭小川夫妇)
1954年5月,郭小川又兼任文艺处副处长,主管电影,8月,他率团访苏。1955年,又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历任党组副书记、作协书记处书记、秘书长、《诗刊》编委,直到1962年9月。
1955年至1956年,郭小川写出了他的成名作《致青年公民》组诗,包括《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把家乡建设成天堂》《闪耀吧,青春的火光》。在执着的努力下,他迎来了第一个创作高潮。1957年他写了九首短诗和三首长篇叙事诗《深深地山谷》《白雪的赞歌》和《一个和八个》,出版了第三部诗集《致青年公民》,1958年出版了第四本诗集《雪与山谷》和第二本杂文诗集;1959年他写了《望星空》等七首短诗、五首长篇叙事诗,出版了第五、第六本诗集《鹏程万里》和《月下集》。
有评论认为,《望星空》“折射了当时相当深刻的社会内容,在大的失误和挫折面前,任(革命者)对自己的生命、意义、命运的新思索,把握和追求,达到了当代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而长诗《一个和八个》则是郭小川在人性探索上达到的顶峰。
1958年10月,郭小川赴苏筹备和参加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在那里工作了两个半月。
1962年10月,郭小川调到人民日报当一名记者,他到处奔走采访,开始了如泉喷涌的第二个创作高峰。他到鞍山、抚顺采访,写出来《两都颂》,继之又到华东、华南、西南采访。在1962年获得一年的创作假期后,他欣喜地南下福建海防前线,又随老首长北上东北林区。1963年春,先赴上海采写《南京路上好八连》,又与王震等同志赴苏州、无锡、杭州、绍兴,又走了福州、黄岐、泉州、厦门、云霄、漳州等地。7月底又西访新疆,在老战友王恩茂的安排下到了北疆的阿勒泰、伊犁,南疆的喀什、阿克苏、和阗等地。
“文革”乱世中,郭小川和杜惠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和迫害。
1970年,郭小川来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四大队五连,年底咸宁干校撤并,大部人员回京分配工作,少数转天津团泊洼文化部静海干校。
郭小川晚年写的诗《团泊洼的秋天》和《秋歌之六》是他晚年最辉煌的作品。
(郭小川《秋歌》手稿)
1975年秋,在纪登奎、王震等的不懈努力下,对郭小川的“中央专案审查”终于以无任何问题结束。10月9日,郭小川回京,组织关系转到中组部,并受到四位副总理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的接见。在经历了周恩来总理、朱老总、毛主席相继辞世的巨大悲痛之后,他的体力大不如前。到10月上旬,他从广播和报纸的微妙变化中察觉到中央出了大事,便焦急地等待中组部的回京指示。他独自搭车到安阳,准备到医院看看病,去省委请示一下就回北京,那时正开三级干部会传达“四人帮”被捕的文件。不知从什么渠道,他得知了这一特大喜讯,激动万分,却无处诉说,吃了安眠药以后又点燃了烟卷,致使睡眠中烟头引燃被褥,郭小川在氤氳的浓烟中驾鹤而去,那一天是1976年10月18日,他刚满57岁。
他曾在诗中写道:
“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化烟,烟气腾空;
但愿它像硝烟,火药味很浓,很浓。”
想不到,这诗竟为谶语!
“全国解放后,我和小川到武汉的中南局宣传部《宣传通讯》当了半年编辑,后又进天津,在《天津日报》工作。1953年进北京,在中宣部还做编辑工作。到1956年我被分配到《光明日报》做编辑,期间在高级党校高级班学习,四年后又回到《光明日报》,到1980年我就离休了。”
“我的儿子郭小林是1946年在你们赤峰林西生的,1950年我生了大女儿郭岭梅,1953年生了二女儿郭晓蕙。”
“我喜欢当记者,经常骑自行车到处采访,有一次我骑自行车一个人从北京到天津采访,中途在杨村的三元村的小饭馆吃饭。你知道现在要想到某个大饭店讨口开水喝是绝对不可能的,可是那三元村的小饭馆主动给自带干粮袋的农民泡茶,倒开水。我对此作了报导,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当时李瑞环同志对那个饭馆给予了极大的表扬和赞誉。从此三元村那个饭馆名声大振,记得那位老板叫刘士安。”
笔者诚恳的向先生请教长寿之道,她老人家笑笑说:“我主要是心大、坦荡、说话直、好挑毛病,但心里不装事。”
笔者趁隙问:“听说到现在您还游泳,这也是您的长寿之道吗?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游泳的?”
“你说的对,我的健康和这个运动有很大关系。”
“解放后学会了游泳。1951年我到广州岭南大学参加全国大专院校系调整工作时,住在岭南大学,女同学们教我的。以后一有机会就游,一直坚持到现在,最早从1953—1954年我都在国务院养蜂夹道游泳池游泳,毛主席也常去游,我还在那个游泳池和毛主席和他的工作人员游过泳,小憩时聊天。因为在延安时,我在毛主席办公厅为毛主席抄过文件。五十年代初在北戴河,还和毛主席跳过舞……”
采访结束了,笔者从仰慕和惊愕、震撼和感动中清醒过来,看到的仍是九旬老人恬静、慈祥的微笑。多么跌宕多舛的人生,老人的心胸是何等宽广,生命力是何等强大,我原以为衣食不愁、养尊处优的人才能成为百岁人瑞,没想到经过战争洗礼,在逆境,在焦灼中生活过的人居然如此坚定的活着、笑傲人生,用她纤弱的身躯成为民族的脊梁。
看到茶几下边有一本订得很随便的约十开大小的本子,里面全是一张张单据,我好奇的问老人家是不是还在管日常的开销,老人笑着说:“你自己看。”我仔细浏览下去,才发现都是捐款收据,是老人多年来为汶川地震、残障儿童、贫困小学捐款的收据,合计起来约一百多万元,可敬的,有慈悲心的老人,您让我感动的说不出话。
车子离开疗养院很远了,我还在回望,可敬的老人家,我发自肺腑的祝您健康长寿!
(2014年11月16日“纪念郭小川诞辰95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现代文学馆隆重召开,笔者应邀参加了研讨会)
(杜惠先生给赤峰人民的敬题)
(杜惠先生与笔者的合影留念 )